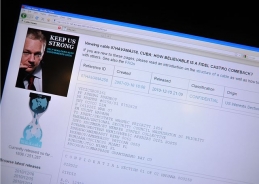(续前期)我在《明报晚报》的专栏写到1980年底。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来香港几年,逐渐认识中国回流香港的媒体朋友,最早认识的是辜健,马来西亚侨生,他在《新报》编新开设的中国版,邀请我写不定期的专栏,他喜欢变花样,于是我用林念、周坦、林尖等笔名写了「民主墙」、「风云人物」、「人物素描」、「特区动态」、「大陆生意经」、「知无不言集」等不定期专栏。
辜健是学文学的,并不喜欢政治,但是生活所逼,也得从事这一行。我与他最「深交」的一次谈话,就是讨论写政治文章的风险,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不要怕东怕西,下决心就去做,要做「反革命」,就做大一点,否则成不了事。但是政治并非他的爱好,所以最后因为所学「专业」而做「反革命」的是我。
后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苏州人吴伟华担任《新报》副刊编辑,我在那里开了每天一篇的专栏,开始栏名是「弹叹谭」,笔名是海木(上海阿木林),写了多年。1990年代再用凌锋的笔名写「界内界外」专栏几年。《新报》换了好几个老板后,终于在2015年7月12日停刊。
写政治专栏
在这期间,我在《明报》蔡炎培主编的副刊以周怀的笔名写了一些散文,不过少之又少,因为那里是人们抢投的园地。进入《中报》以前,已经与傅献堂比较熟悉了。因为他们需要人而我一时来不了,后来就推荐我太太去做中国版。她对媒体认识很少,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但是为了生计,虽然身体不好,她还是上班了。我在下班后赶来帮她做,因此她主要负责中国版的校对工作。我也写相关专栏,从1980年9月1日开始,用「林念」的笔名每天写一篇「人物」专栏。当时中共政坛因为要清算文革而人事大动荡,尤其大批老干部平反复职,我对他们的生平与文革的遭遇相当熟悉,因此每天有东西可写。到了第二年,改为比较灵活、不限于人物的「新闻述评」,再后来用王山笔名写《长城内外》专栏。
为了写政治专栏,我也下了不少「投资」,买了许多参考书与政论杂志。其中最重要的是买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共人名录》,定价美金四十元,加上运费,似乎接近五百港元,是我的月薪三分之一。又买了黄震遐编着的《中共军人志》。我除了个人订了北京出版的《新华月报》,还订了好多年台湾出版的《中共研究》杂志,但是我主要并非看他们的评论,而是关注里面报导的台湾监听中国地方电台的相关内容,尤其人事。对中共的观察,最重要的是人事变化,因为「干部决定一切」也。随着经济情况逐渐好转,我买了许多工具书,以后我的写作,都是靠自己的小图书馆,不必依赖他人。
那时的《中报》地点在湾仔告士打道,马师道与杜老志道两个路口之间,离开新都城的家不远。两个人都上班,经济状况好了一些,但是因为下午与晚间上班,就少了与小孩子接触的时间,对功课的监督少了,也还没有能力去请补教老师。
担任副刊编辑
1982年,我正式进入《中报》,编副刊,也就是具有香港特色的几百字小方块专栏副刊,位置固定,比较好编。其他时间帮助太太编中国版。当时编辑月薪1,500元,另外给我写每天一篇的副刊专栏,每月700元。这是我有每天一篇小方块副刊专栏的开始,内容海阔天空。专栏定名为「无为集」,因为我欣赏老子的放任无为,用的笔名是「林桦」,比较接近真名,希望有比较固定的笔名来逐渐打响名号。我在《中报月刊》也有每一期的专栏,笔名是「马木」,暗批中共的「不仁」。
《中报》后来也有台湾式的副刊,接纳比较长的文章与诗词,也由我担任编辑,自然有些「请托」的稿子,不过我很谨慎,不能因为讲人情而败坏水平。请托的多为中国来港的侨生。其中用过当时在《人民日报》任职的徐刚(六四后曾流亡法国,但也有很大争议)。自动投稿的有后来出任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的颜纯钩(慕羽)的文章。
因为担任副刊编辑,也认识一些香港土生土长与上海南迁香港的专栏作者。当时稿费高低看名气大小,所以老板请不起大名气的。南下文人中有过来人、凤三等作者,已经垂垂老矣,靠这些微薄的稿费维持晚年生活。由于他们写的有许多都是上海的陈年往事,也在各报有许多重复而逐渐过气被淘汰,后来听闻过来人还曾因为希望留下专栏维持生活而给编辑下跪,闻之唏嘘,也为自己敲下警钟。
也在这一年,认识了《星岛晚报》的文坛前辈董千里,他是副刊编辑,因此我也用不同笔名写不同文章,「周怀」政治性,「浮生」是散文,「木佬」写怪论。这期间,还有《财经日报》创刊,负责人是来自《明报》的黄扬烈,我也写过几篇,报纸没有维持太久。黄扬烈后来进入《经济日报》。因为编副刊,也认识了李默。她从事电影评论与宣传工作,负责找些作者观看即将上映的试片,我是外行,也缺乏知名度,她没有嫌弃,经常通知我去看。她是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因此可以用普通话与我沟通。据说有的娱乐版专业作者会收红包,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是外行,即使写些电影评论,也是在副刊专栏而非娱乐版的专业评论。听闻即使电影差劲而无法称赞,也得在电影下档前一天才批评,避免影响票房。我看过好几部台湾电影的试片,例如《玉卿嫂》、《竹篱笆外的春天》等,也写影评。有一次梁英明来香港,我还带他看了《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试片,他很高兴,那时在中国是没有机会看到的。
接触台湾编辑
《中报》后来办美国版,有的版面在香港编辑,因为香港的人工比美国低。于是我被调去编美国版的副刊。美国《中报》的班底都是台湾人,因此我得以接触一些台湾人,副总编辑李义仁从美国纽约来香港坐镇。香港是广东话的世界,尤其是「报纸佬」,他与我可以用普通话沟通,我也协助他与香港本地的报人沟通,因此我们接触较多。《中报》总编辑俞国基从美国来香港考察多次,我们也交谈甚欢,尤其他讲话风趣,不时爆出傅朝枢的笑料,例如傅为了说明他比查良镛更受邓小平重视,老是指着手表说邓小平接见他的时间比查多了几分钟。其实这不就是中共利用人性中「争宠」的劣根性对媒体进行「分而治之」的统战手段吗?
在编美国副刊的过程中,我了解了一些台湾的文化界情况,例如台湾的乡土文学,第一次接触到杨逵的名字。我也在美洲版的中报写专栏,介绍香港,笔名「孙耳」,取「顺风耳」的谐音。我还在副刊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介绍中国作家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那是难得描述中国经济改革起步的作品。张洁是我在人大的同届同学,不过她读的是计划统计系,当时并不认识她。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也是人大侨生的薛瑞珍是她同学,所以我也了解有关她的一些信息。
我的同班同学苏叔阳也在差不多时候写了《丹心谱》(歌颂周恩来)而出名,我也在《明报》副刊写了介绍他的短文。俞国基、李义仁在1983年离开美国《中报》,去了美洲《中国时报》,我也跟着在美洲中时以「李明」的笔名写评论香港的专栏。后期在美国的《中时周刊》写评论,用的是在《信报》的笔名「凌锋」。这些都让我存了一些美元稿费,但也被香港新华社扣上「台湾背景」的政治帽子。
我在《中报》工作最重要的是接触了台湾党外思想,因为俞、李都是同情台湾党外,批判国民党的专制制度。当时我在香港与右派关系不错,因为有「反共」的共同点,但是并没有因此就敌视党外,只希望台湾能团结抗共。
在《中报》时,内部有规定国民党有五个人不能骂,共产党也有五个人不能骂。因为一直赔本而不断改版,越改越失去读者,香港《中报》先关门。后来传说美洲《中报》还接受中共的金援,六四后站在中共屠城立场也不奇怪了,以致在美国也失去读者,这是后话。傅朝枢去世时,我已经移居纽约,到底有一场宾主关系,虽然本人与他不认识,但是与傅献堂与他的几个妹妹都熟悉,所以参加他的告别式,见到傅家几位兄妹,他们自是感到意外。从此进一步改变了我的命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