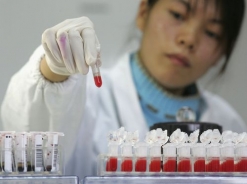长大后,忆起乡下姐姐手里抛起的一个个小布囊时,似乎看见了一朵朵缓缓升起的莲花。当然,现在已见不到乡下小孩玩小布囊的游戏了,儿时的玩伴们也不知奔波到哪儿去了。
小布囊握在手心里,从手里充实到心里,我幼小的心灵像握了整个天地。掌握了天地,更要小心翼翼,布囊里的沙子是松散的,不受拘束。掌心变了形,囊里的东西随机流动,窸窸窣窣的声音经过手臂传达胸臆,有丝丝暖意。若囊里装的是稻谷子,连壳带米的谷子不好侍候,心里既惊且喜,手掌稍一用劲,谷子互相推挤,不等聒噪的声音传到胸臆,心里已是天崩地裂,沛然莫之能御。正等待驾御天地的壮烈时,谷子的推挤已因布囊里空间的自然变化,消失于无形。
手掌里要有握着小布囊的机会,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得到的。
小时候,乡下流行着小布囊的游戏,是女生们的专利,因为只有女生能从母亲、姥姥那里学来针线的窍门。瞧着姐姐们不知从哪弄来各色的布块,缝成了一个个小布囊,布囊里装满沙子或谷子。冬天刮起了寒风,或是夏天来了西北雨,女生们没地方玩了,小布囊的游戏就是她们的拿手绝活。
姐姐们揪着伴,藏在哪家窗前大床铺上,围成圈圈,几只眼睛注视着小布囊从翻转的手心手背升起落下。一人玩着,旁边的人应着手势,从一数到九,唱着有字无音的谣。布囊要离了手,落到床铺上,就换人玩了。我一个小男生挤在圈圈里,只有凑趣的分已雀跃不已。记得那谣唱的是:一点鸡,二点鸭,三拍胸,四打架。后面的词,全忘记了。
一个午后,田野里下着细雨,姐姐们躲到檐下玩起布囊游戏,我瞧见一只蝴蝶在升起落下的众布囊里飞舞,猜着那是桂花姐姐从母亲的头巾裁下来的,让我也想到了曾祖母长长的缠脚布。趁着曾祖母在谷场晒缠脚布时,怯怯地向她要一小节,曾祖母却笑呵呵地剪下了长长一段,我兴奋地把缠脚布交给了桂花姐姐。这段长长的缠脚布让我跻身姐姐们的小布囊游戏圈圈里,当那个缠脚布缝成的布囊在姐姐们手里升起时,桂花姐姐摸摸我的头,把歇着的布囊塞到我手里。
握着小布囊,握着乡村的泥土气息,握着重重的善良与朴实。当我握着布囊的小手长成了大手掌时,手里的布囊也变成了鼠标。
如今不见了小布囊,肯定是曾祖母把缠脚布也带走了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