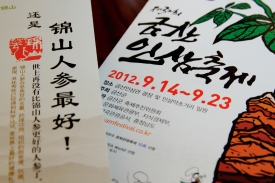一歲的女兒在我懷裏喝奶,兩隻澄亮的眼睛和我的對望,看得很深很深。那是產後六小時第一次餵母奶起,我們之間時時相互尋找、相互確定的凝望。
透過記憶之眼,我看著小小的我窩在媽媽懷裏,摸黑吵嚷著:「媽媽不要睡,聽我唱相思燈!自-古-紅-顏-多-薄-命……」剛從舅舅家的電視布袋戲學來這首歌,三歲的我急著唱給媽媽聽。那晚,媽媽極度睏倦但慈祥的笑聲安撫著我入夢。當時的我不會知道,這是少數我對媽媽的愛的鮮明記憶。那個夜晚過後,媽媽柔軟懷抱的溫度,一如懸在驢子面前的紅蘿蔔,讓我終日追逐卻始終懸宕。
始終沒說
窮,所以大人為了過日子已身心疲累,加上我有個家族長女的大姊、懂事的獨子哥哥、伶俐可人的二姊,和乖巧的么女小妹,媽媽的疼愛很難輪到我。我卡在尷尬的位子,頂著一頭西瓜皮幫妹妹綁好烏溜溜的馬尾巴,再趕忙追逐二姊長長辮子上的蝴蝶結。
不曾對媽媽透露,我有多想留長髮,她已經夠忙了,屋裏屋外,一家老小,還有田裏從不止息的苦活兒。閉上嘴巴,我跟在媽媽身邊,蹲下洗衣、彎腰下田,媽媽簍小蝦我採水茼蒿,媽媽熱油鍋我揀菜洗菜。
沒和媽媽提過,當姊姊用媽媽精心烹煮的八寶甜湯在招待來家裏玩的同學時,我正品嚐一份酸酸苦苦的滋味。那天,同學釣魚的腳踏車隊經過我工作的田邊,烈日下俯身拔除莠草的我趕緊把頭垂得老低,祈求同學不要認出田裏那個滿身泥巴的人是我。而他們,終究留下了一陣嬉鬧的笑聲給我。
我都沒說。我以為媽媽看得到我勞動的身影。可是,沒有發出聲音的我,還是沒有得到她的注目。乖巧而刻苦為了什麼,我不知道自己有何價值。
火爆青春
很快的,在青春期的作用下,我找到了一種方式來博取注意:那個早晨,媽媽忙得太晚叫我起床,我在她面前摔掉了她匆忙打理的便當。呵,奏效!媽媽只是蹲下來收拾飯菜而沒有罵我,甚至好像為了我的舉動而難過。往後的五、六年,類似的火爆劇隔一段時間就上演一次,以確保我在媽媽心中起的些微作用不要散失。粗略的對待、僵硬的依從,隨著我慘綠的年少歲月演變成我和媽媽的相處模式。天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那只不過是我索求關愛的愚蠢方式。讀書,為了離家,那是最正當理由。
離開家自力讀書,怕在電話裏沒話說,我不喜歡打電話回家。回到家依然只會趴下來拖地、踮腳剪竹籬笆,不會說柔柔軟軟的話,那些撒嬌的事,姊妹們向來做得比我好得多。
失落的圓
我還是沒說,媽媽也不會知道,那個依然勤快的身子裏有一個缺口。我像個缺了一角的圓,轉向感情世界尋找失落的缺口。一個不愛自己的人卻說著「我愛你」,讓看似繽紛實則混亂的情感,掩飾我心底的荒涼。青春已近尾聲的那年,幸運地遇到了第一個從心裏願意嫁給他的人。那麼,也許生一個女兒,讓我全心照顧她,給她我所能給的愛,我就會知道媽媽的愛是什麼?
先生暖暖的手握著我的手,陣痛儀器列印出的疼痛指數已高過紙張邊緣了。我閉上眼仔細品嚐疼痛──這黑色的痛啊,像暗夜疾行的列車駛進了幽深的隧道,但不及心底缺口處的黝暗。進產房,女兒在八分鐘後與我們見面,醫生高高舉起圓滾滾的粉紅嬰兒,我看見那條流通血脈、粗大厚實的臍帶,真真切切連接著我和她。就在那一刻,我的心翻湧起幸福的巨浪。我知道列車已衝破了幽暗。我的身體、我的心靈沉浸在白亮、輕柔的喜悅裏。汗水縱橫的臉上交錯著止不住的淚,我想這就是答案了:母愛是天性。我的臍帶也曾和媽媽相連,媽媽也曾給我圓滿的愛,只是,我的嫉妒和埋怨鑿出了我自身的缺憾,我對愛的渴求啃噬了曾經圓滿的愛。
為母則強
有了女兒,我和媽媽有了聊不完的話題:女兒四千公克,原來我自己也是四千五的大寶寶;女兒四個月大長牙,媽媽說五個孩子就我最早長牙,長牙時牙齦痛癢,我常常把媽媽的乳頭磨咬破皮,她擦擦血漬,換一邊繼續餵哺;女兒睡前哭嚎一兩個小時,將近周歲才改善,媽媽說我直到三歲認了乾媽才變乖。因為女兒,我得以知道媽媽記得每一個小孩的成長細節,其中包括我。
女兒全然的依賴和單純的愛,直接而強烈,每一天她都用她獨特的方式在教育我、訓練我──要堅強,別軟弱;要寬容忍讓,不可粗率相待。常常覺得在她出生的同時,帶著我此生的功課表,而小小的她給了我大大的功課,第一堂是:她只有我這個媽媽,別人無法給她媽媽的愛。
一天一天,我緩慢地學著珍視自己。缺口還在,但我依稀看到療癒的希望。為女則弱,為母則強,是愛帶來了力量,讓我這個不及格的女兒有力氣學習做一個母親。
十幾天沒聽到媽媽的聲音,我打了電話回家,「妳想到啦?」現在反而是媽媽用淡淡的埋怨,在向我撒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