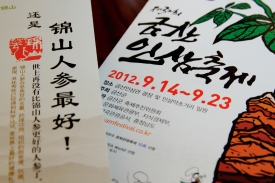我的陶笛老師是一位盲人音樂家,他指導我時,彷彿是用X光透視追蹤著我的舌頭、橫膈膜與手指的移動,就像武俠小說中行走江湖的盲劍客,出招精準神奇;他的「打狗棒」一點地示意我暫停後,吹奏祕笈旋即源源道出。在對音樂的詮釋、感情的表達與線條處理上,動人心弦。他將耳朵的潛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他請製笛師傅寄來三把手工笛供我挑選。他推薦我使用的那一把音色、氣量都十分適合我,我卻因那把外觀土氣而遲疑,而他絲毫沒有這方面的困擾。音色最好的就是這把,有甚麼好猶豫?他真的是閉著眼睛下的決定都比我明智。明眼人的決策還不如一位盲人。
我的老師不會被舞台的表演花招所吸引,不受制於觀眾的反應,音樂本身是唯一的專注,自然容易獲取音樂的神髓。樂器的音色是最重要考量,長相反倒次要,因此選購時避開了華而不實的陷阱。他交朋友也與這個人看起來順不順眼、稱不稱頭無關,互動之間可以感知對方的個性、談不談得來,於是他交到的朋友都是最真的朋友。
商品、傳媒再再鼓吹著外在的擁有可以帶來的自豪。便利商店裡販售一些流行性的愛情書籍,封面繪製的美女除了髮型、服裝不同,長相大同小異,好像是同一對爸媽生的。內容不外乎與富家子、總裁等的戀情。「總裁」的誘人職稱左右著人類無價的感情。電影《Bright Star》中,詩人濟慈在深情裡看見的神聖,於今當真為笑談了。
其實別人如何看待你、工作頭銜夠不夠響亮,與自己實際生活過得好不好實在沒有甚麼關係。人到底是為我與健忘的,一謝幕各自回家,關心的不就是個人方圓幾公尺以內的事情嗎?每當我看著海鳥在蔚藍裡低迴,在風中遊弋,那麼自在,我想人常常給自己心理上添了很多不必要的包袱吧。
原名Samuel L. Clemens的幽默、諷刺大師馬克.吐溫尖銳地說:「頭銜──這也是一種人為的東西──是衣冠的一部分,頭銜和羅衣掩蓋了一個人的卑微,使他顯得偉大、出眾,而骨子裡,他卻是平庸之輩。頭銜和衣冠能使傾國下跪、去頂禮膜拜一位君主,其實,要不是他那身衣冠和頭銜,他會落到社會的低下階層,被淹沒並消失在凡夫俗子的人海裡……」看看原文,更覺犀利:Titles──another artificiality──are a part of clothing. They and the dry-goods conceal the wearer’s inferiority and make him seem great and a wonder, when at bottom there is nothing remarkable about him. They can move a nation to fall on its knees and sincerely worship an Emperor who, without the clothes and the title, would drop to the rank of the cobbler and be swallowed up and lost sight of in the massed multitude of the inconsequentials……)
「世情惡衰歇」,人們總是喜愛榮華或「高人一等」的人。關於這種普世心態,泰戈爾的敘述讀來就令人莞爾許多:
玻璃燈罵瓦燈沒資格跟它稱兄道弟;而當月亮升起時,玻璃燈卻滿臉堆笑,稱呼月亮──「我親愛的,親愛的姊姊。」(While the glass lamp rebukes the earthen for calling it cousin, the moon rises, and the glass lamp, with a bland smile, calls her, ──“My dear, dear sister.”)
而泰戈爾欣賞的典範以輕巧小詩表現如下:
星星不懼自己螢火蟲的形象。(The stars are not afraid to appear like fireflies.)
偉大者不懼與渺小者同行;居中者卻避而遠之。(The Great walks with the Small without fear. The Middling keeps aloof.)
我們在卑微時所表現的偉大,方始近乎偉大。(We are nearest to the great when we are great on humility.)
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中認為理想的哲學家是:「能愛好人生而不過度,能夠察覺到塵世間成功和失敗的空虛,能夠生活於超越人生和脫離人生的境地,而不仇視人生的人。」
如此和諧的生命情調,令人心神嚮往。走向虛榮,矇蔽愈深,煩惱也就愈多。但願自己可以多長些智慧,真心地生活,穿透浮華的迷妄,作一個真正耳聰目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