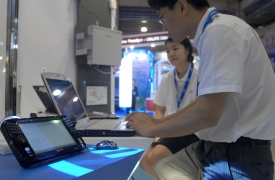「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傅雷
* * * * *
曾经有过那样珍贵的机缘,参加钢琴家傅聪在台北举办的大师班。音乐系学生、知名学者教授齐聚,他指导学生弹奏,我是为数众多的观众之一,我的母校音乐班师生也专程北上观摩。
傅聪在第一位学生卯尽全力弹完后,走到钢琴旁简要说明了一下,随即坐下来示范。当他的手指一触琴键,不过几个小节的光景,全场登时发出无法自已的惊叹,那种整个灵魂被收摄、只能任由摆布的赞叹!
我更是惊呆了,呆到忘记写下这位学生弹的曲目,甚至质疑就在眼前发生的事实:他们弹的是同一架钢琴吗?!
不过小弹就已赢得全场掏心挖肺的倾心,傅聪的反应竟是:
无─动─于─衷!
甚么都没听到似的,行止、表情无丝毫得意。也许是见多不怪、习以为常也好,但我更确信的是,不管观众有多少、赞美如何排山倒海涌来而不被淹没的原因是:
他心里只有音乐。
因为这个表情我见过,在我高龄八十几岁的绘画老师身上。当他们一进入艺术的世界,已然出世,周遭所有一切都成了外物。
傅聪认为,学音乐就是在读「谱」,研究音符的深层意义、作曲家想说甚么,因为每一个句法都是有意义的,否则沦为浮泛。没有后面的内涵,即便弹出了那个音符,你仍然没有「找到」那个音。
他比划着手说,就像文学中的伏笔,谱里面其实有很多「暗示」,预告行进的方向。旋律线的流动不就像雕塑的线条吗?
第二位学生激动地弹了马祖卡舞曲。他热切地脚打着拍子提醒:第一拍跟第三拍一定要分开。
「你看跳马祖卡舞蹈,脚是会飞起来的那种。」
学生弹到热烈处,他脱口而出:
「不要打钢琴!不是用打的……对钢琴温柔一点。」
观众不禁莞尔。
傅聪从进场到现在,一直让我觉得,他彷佛忘记有这么多观众屏息盯着他。他眼里只有音乐。
此时,他好像才记起现场还有别人。
他转过头来对大家说:
「音符不是音乐,音乐是有内容的。」
他解释,像说书,如果从头到尾都同一个语调,观众肯定跑光光。说故事不会平铺直叙,总是虚虚实实,不要一直都是实,这样才会有转折、有惊奇。有些音乐会,有听跟没听差不多。要弹出会「说话的音乐」,音乐表情才丰富。
「你的音乐在说些甚么呢?」他望着前方,问自己也问大家。
第三位学生弹奏肖邦的「练习曲作品10第3号」,俗称离别曲。
「你真的是把它当练习曲啊?练习曲也是音乐,要有passion!」这是傅聪听完全曲,毫不掩饰的第一个反应。
这首肖邦最喜爱、自认写得最好的旋律,傅聪认为一般都弹得太慢了。其实慢的,才是最难弹的,因为牵涉到力度及句法的掌控。
「他的音乐是可以哼的,从不婆婆妈妈。」傅聪轻轻地哼了起来。
他全神贯注地教导,学生每弹到一个乐句的结束,他马上提醒:呼吸、这里要呼吸!
学生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众目睽睽,在大师指导下弹奏的压力不小啊。
「你的左手不呼吸的。」傅聪摇摇头,接着以国画中的留白比拟音乐中的「呼吸」。
谈到画,傅聪坐在钢琴椅上旁若无人似地兀自独白:「一切音乐表现,一定有个合情合理的原由。」
他说,大艺术家,像大画家之于色彩,总是以一物衬托另一物……停顿了半晌,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大师班三个半小时下来,观众都有点累了,以他的高龄,他却仍在音乐的世界里驰骋,像一位意气昂扬的老将。他坚持版本的选择,痛恨任意改编原作的人,因为:
「没有一个细节不该不根据谱的标记弹。」
他的严谨自始至终不放松:
「虽然这里有两个降B,但它们绝不会一样!」
这就是我看到的傅聪。没有交谈过,却留给我对音乐、对人文、对艺术深深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