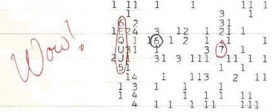他的表情很奇怪,因为这种问话实在是闻所未闻,
可那小钢炮的心防却即刻地瓦解了……
廿余年来,我一直和青少年生活在一起,于教育现场里我经常脸不红、气不喘地向学生们推荐自己的「绅士」影像;但最让学生受不了的是,我偶尔会调侃却不失诚挚地问孩子:您爱我吗……
在8月底,我接到了调至新学校服务的派令,因为已非初任,所以没有任何排场与交接的介绍会,隔天,我就单枪匹马地上班去了。到了学校,才发现昨夜的一场急雨,竟然让校园变成水波微兴的湖泊。时值暑假期间,又是清晨,校、内外悠悠然杳无人迹,瞧着脚下全新的阿瘦皮鞋正犹疑的当儿,适时的,接我的荣华老爹打着赤脚地在彼岸招呼着,他准备抛过来一双拖鞋解我的围。
这场景有些幽默,瞻前顾后遐思之际,海风轻送,眼前的湖泊涟漪阵阵,念头一下子又转了回来:既然下了海,哪有怕裤子湿的理。当我发亮的新鞋子才涉入及膝的水中时,竟听见背后传来嘿嘿的笑声,我回头看见有位顶着一头黄发、右手指夹着纸烟,直觉上是游荡了一整夜的瘦高少年正转身准备离去。
两个月后调教您为绅士
过了些天学校开学了,我特别到后门去迎接也同时认识下乌麻园的孩子们。招呼了一群群的学生后,有位染了发而似曾相识的孩子,他穿双拖鞋却空着手两眼迷茫地晃了过来。我迎了上去,熟门熟路优雅而正式地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校长,很高兴认识您,请教您的名字是?」黑黑瘦瘦的孩子咧着嚼多了槟榔的黄板牙,困惑地睨着我并告诉我他叫「章仔」。
章仔接着不吭声地打量起我的新领带、毕挺的衬衫、西裤,当视线移至皮鞋上时,他又发出熟悉的嘿嘿笑声。我也笑容可掬地告诉他:「我是口湖小区的绅士,很有学问又喜欢学生,章仔,我会很疼爱您的!」他一脸胡涂,我想他还真搞不清新校长到底是哪一路的?但我还不放过他,续道:「两个月后要把您调教成一个绅士!」当章仔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我轻轻对他施了个礼,便飘然离去,继续寻找新的搭讪对象。离开时,我的眼睛余光看见章仔迭着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在太阳穴旁扭转着,指着我用唇语告诉他的同学:「疯仔!」
这是我第二回和章子照了面。后来,我得知章仔一直是学校头痛的学生,绰号叫「小钢炮」,他脾气暴躁,拗得很,上个学期就经常性地逃课、喝酒、抽烟,晚上总是一、两点钟才回到家,很难预料他会闯出甚么祸来! 三个星期过去了,章仔穿上了鞋子、染回头发、多数日子能准时上下学,但是仍然抽烟、上课打瞌睡、晚上游荡、嘴角偶留有槟榔残渣。显然地,他还不像个绅士。
愿意为您所爱的人做两件事吗?
有日,章仔在校园里游荡被我碰上了,他身上散发出的烟味引起我的注意,我叫住了他:「谢谢您这些天来能准时到校上课,章仔您爱我吗?」他的表情很奇怪,因为这种问话实在是闻所未闻,可那小钢炮的心防却即刻地瓦解了。他的脸扭曲一红,略为迟疑地说:「爱!」这单字似乎是从黄板牙缝中蹦出来的。
「太好了,既然爱我,您愿意为您所爱的人做两件事情吗?」我得寸进尺地一口气提出两项请求。章仔则小心翼翼地思考着,当听了其一是要为他所爱的人把烟戒了,其二是跑五圈操场练练身体等两件事后,他开始犯犹疑了。见此,我深情款款地又说:「您刚刚才说过爱我的,怎么……」我的话还没说完,小钢炮那双浸过倒灌海水的脚快跑如飞,他似兑现誓约般老老实实地跑了五圈操场。身体是练了,但后来我知道烟他还是照抽不误。显然的,小钢炮爱我是不够深刻的。
又有一次小钢炮逃课,逃了课依照家长到校伴读的程序,他的桌椅先是被搬到了校长室,很快的他也被找了回来。师徒此时相见,我以无限惋惜的口吻询道:「章仔,您还爱我吗?」小钢炮气呼呼地不搭理我,他知道只要回说不爱我,我会纠缠地说理直到他说爱我为止;如果说爱我,小钢炮更是清楚,我底下的话必然是:「您怎么忍心让您所爱的人伤心!您愿意为您所爱的人去把二楼的大、小便斗刷洗干净吗?」三个月来这样的对话与工作辅导,我们已经演练了无数次了,所以,小钢炮深知「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道理。
换换话题,找到改变的力点
有天,章仔搭我的便车回下仑,我别有用意地问他:「阁下喜欢哪位老师的课程?」他很高兴我没有问他爱不爱我的选择题,因此,轻松愉快地于他还没回答前却先提出问题:「甚么是搁下?」我看着后视镜中小钢炮闪动的眼珠,便神采飞扬地教起书来:「是阁下,没有提手旁,它是绅士用语,因此,我称呼您阁下。」章仔似乎懂了,他回应我校长阁下:「我喜欢吴明姿老师的历史课。」章仔和我一下子都找到了改变的力点。
翌日放学后,章仔在马路上公然抽烟,又被逮到了,主任温和却不免失望地和章仔一起整理这几天的账目。我们正深深地叹气时,吴老师刚好经过,她停了下来并低柔地问道:「怎么啦?」。这一回章仔没有提问,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英雄气短地哽咽起来。顺了势,主任攀着章仔的肩膀和他聊了开来,两个男人的声音低得让我听不清楚谈话的内容,但是,我知道这必然也和教育与辅导那档事有关。
章仔真的被许多师长疼爱过,可惜的是,章仔于三上时,因为家庭经济的需要中途辍学做生意去了,这期间学校透过许多渠道协寻,但还是没把他找回来。匆匆四年,一届届的孩子们来了又走了,章仔却是我任内至今唯一中辍的学生,因此,我常会温馨地想起他来。
上周三中午,我拜访友人后驱车回校,当车子欲转入学校大门前,忽然看见一骑摩托车载着太太和孩子的年轻人,他应是刻意地放慢了车速转过头去眺望着校园,那神采似乎正在叙说着某段时光、某个故事。会车时我心头不由得一震,那黄板牙……是章仔!我快速地放下车窗,瞧着后视镜并拉开嗓门大声地呼唤:「章仔!您还爱我吗?」只是,窗外海风猎猎,而那青年早去得远了……